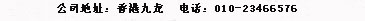舌底朝朝茶味香张喆
来源:舌头口疮 时间:2021-3-1
呼和浩特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://m.39.net/pf/a_4477495.html舌底朝朝茶味香张喆。这是中国古代河姆渡文化的一个重要遗迹,这次人工种植茶树遗迹的发现,将传统认为的中国先民开始种植茶树的历史又上推到了年前。年,对我们来说,也算得上“恐龙”级别的时代,用咱老百姓的话讲: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茶叶在先秦以前时代,是直接食用的。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,茶是一种能够增加营养、并驱逐毒素的好食材、好药材,所以,他们直接是用来入口吃的。由于茶叶的苦涩,后来的古代居民就开始尝试将饭菜跟茶叶混在一起食用。还要加入各种调味作料,煮成茶粥来吃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国两晋时代,人们逐渐开始不在茶叶水中混入粮食,而是直接饮用茶水直到今日了。出门在外,走到亲戚朋友家,到处都有热茶招待。清汤白开水的时代,早就过去了,乏味的水,没有人喜欢喝,一杯茶在水,解乏除困,齿香生津。在我们家里,无论男女老幼喝茶,儿童一般喝淡茶,茶叶放得少,在夏天防止上火便秘。而我的父母在日常最喜欢喝浓茶,特别是我的父亲,他有两大嗜好,一为杯中酒二为闲情茶,可谓是无酒不欢,无茶不饮。不管走到哪里,一两个小菜招待入盘,泡上浓茶一壶,酒杯一举,他就高兴地忘了回家。从我有了记忆起,当小学教师的父亲就爱喝茶,一旦放下饭碗,他就会端起茶缸饮几口,然后舒服地伸着懒腰,真可谓是无茶不欢,白色的大瓷茶缸是他的御用。每天早上一下了床,父亲的第一件事,就是烧开一壶水,抓上一把茶叶,扔进大瓷缸中,淋上沸腾的开水,盖上茶盖子,然后才开始慢慢地洗漱。那时的茶叶在我印象中,都是些不知名目的茶。父亲多半是从街市中,流动的小贩摊上购来一斤两斤的,叶片很大,浮在水上的叶片很黄无光泽;偶尔县城工作的姑父也会拿过来一包好茶,有时是信阳毛尖,有时是龙井,有时是高山茶……父亲通常会把这点好茶密封好放进柜子中,视若珍宝,除了家中有客人来,他很少放开胃口喝这些好茶。流水的日子往前奔腾不息,不管是学校教书,还是耕田耙地,或是插秧秋收,我父亲的身边都有一大缸子茶水陪着他,从山沟到旱地,这些茶水陪着走过一年又一年,走过焦头烂额,走进平和安详。闲来无事时,父亲爱钓鱼,他通常背上一大军壶泡好的茶;行走在青山绿水间,父亲一坐就是一个下午,边钓鱼边饮茶,一个人其乐融融,他沉静在山水田园诗意的生活中,“醉”在茗茶的幽幽乐趣里。待到我适婚的年龄,家里的“媒人”来了一拨又一拨,我自认缘份没到,岿然不为一张张巧舌所动,凭你说的天花乱坠。一个偶尔的机会,一个远亲带来姓杨的小伙子上门,他自我介绍了一番,说是来提亲的,小伙子长得端端正正,更让父亲高兴的是,他竟然提了两包茶叶两瓶好酒,茶叶可是我们本地的名茶——信阳毛尖,这在当时可是名贵奢侈的礼物呀,直把我父亲喜得当场泡了几杯。这开春的毛尖果真与众不同,芽叶大小相同,一杯沸水下去,浮起来的茶叶绿莹莹的,叶尖丰盈,再看一眼,柔软的的感觉立刻沁人心脾,茶水的颜色嫩黄中带着一丝淡淡的绿,父亲一边饮一边说:“这茶叶香呀,香呀。”留下他们一起吃饭,杨姓小伙总是主动给我父亲敬酒倒茶,一再许诺只要父亲爱喝茶,他以后会经常给我父亲买。趁着父亲高兴微醉的当儿,他与我父亲又聊起了茶文化,说起中唐时期的陆羽号称“茶圣”,他所作的《茶经》,是世界上第一部饮茶专著——愣是把我吓了一跳,想不到身边竟有人如此懂得茶文化的源远流长。这倒也罢了,他们偏偏还聊起了资料上没有的记载,说起有一档央视,每晚讲史,有一晚讲起女真人时期,奴隶可以用茶叶来换,几把新茶可以换一个奴隶。可见那时的茶叶已经作为价值币在市面上开始流通了,且价格不菲。听到他们的这些言论,我真是受益匪浅。两个兴致很高地男人,又聊起最有影响力的诗人白居易,白居易对茶怀有浓厚的兴趣,一生写下了不少咏茶的诗篇。他的《食后》云:“食罢一觉睡,起来两碗茶:举头看日影,已复西南斜。乐人惜日促,忧人厌年赊;无忧无乐者,长短任生涯。”诗中写出了他食后睡起,手持茶碗,无忧无虑,自得其乐的情趣。杨姓后生侃侃而谈,借着酒劲茶劲,他把我父亲身上的文人酸迂气全都勾了出来,一时之间,堂厅内谈笑风声,看模样,两人恨不得八拜之交称兄道弟。他一再帮父母盛饭夹菜,饭后又收拾碗筷扫地泡茶,直把父母看的心花怒放,真是丈母娘看女婿,越看越欢喜。众人此时的情绪,因为茶与酒的媒介作用,得到最好的轻松释放,捉襟见肘的贫困日子,因为有了茶水飘香的气味,有了茶水解乏除困的功能,日子才会滋润有声,生活渐入佳境。我那时在纺织厂上班,周末回家,父母说起这事,还在一个劲地夸杨姓后生,要我同意这门亲事,说这位后生打着灯笼难找,勤快干净还会办事,又懂人情世故。我感觉父母的话不可思议,回到工厂上班后没有再理会。谁知隔了半个月回家,父母再次告诉我,他们答应了这门亲事,看着放在桌上贵重的酒与茶,想到百孝不如一顺,我同意先看看再说。这一说看看不要紧,双方订下集市见面,若无议异,当场就在小酒店吃饭。去集市的这一天,见到姓杨的小伙子,长相倒是有点小帅,但是个头不如我的意(我个子大),可是我父亲已经坐在人家订下的一桌酒席上,酒席正中间依然摆放着父亲喜欢喝的茶叶两盒与两瓶白酒。就这么着,这姓杨的后生后来就成了我老公。结婚之后,我老公逢年过节依旧是茶酒孝顺。当然,他总是年年如此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这买茶,买酒的档次也节节提高,从最初的一百多元到如今的四百多元,每一步的变化,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上,每次逢人就夸我老公孝顺,说他的眼光是如何的了得,看人看的准。嫁进杨家门来,我才发现自己无意中成为“地主”,坐拥一大片山头,山头上栽满了茶树,每株及腰,一垅垅的梯田式,一年四季常青。站在茶园的中间,清风徐徐吹来,望着一望无垠的绿涛婆娑,我感觉自己成了君王,面对层层叠叠的山脉,我有了一呼百应的威仪。不仅如此,我们那一片的山脉,我们整个信阳市,许多人家都有茶园茶山,一眼望不到头,林场的茶园面积,更是以万平来计算。每年春天,春茶出来了,家家户户发愁,街道上的小贩催得紧催得急,但摘茶的人不多。好在这时候,河南以北的农村人活不多,她们出来了,这些女人男人自带“坐骑”,乌泱泱一群,分散在各大茶场之地。如若采摘头道春茶,那就是费时费力的活儿,只能摘下一片叶尖,一天下来,摘两斤的人算是快手,一般来说,各茶场给的工钱每斤是40-50元。但若过了春茶再来采摘,要求不那么严格,叶片多而密,只要嫩,都会摘下来,通常每斤是4到5元,一天摘30斤左右不成问题。相比较大茶场来说,我们的茶园是小的,所以只有自家亲朋来摘一些,春茶时卖个好价钱,过了头道春茶,便是自家人喝了。至于秋茶,家里人手不够,只能任凭茶树自己疯长了。炒茶是个费力的活,这个活儿很少有人会干,一般的人家请一些师傅。好在我家公爹是个炒茶高手,在一口倾斜的大铁锅前,通常只见他高搀起衣袖,轮起大竹扫把,不停地在锅里炒着,叶片翻转不停,这道叫着杀青,杀青过后,感觉叶片发软,便熄火把茶叶倒入一个大簸箕,趁着叶片发软,一家老少揉捻成卷,再倒入锅里均匀受热,再翻炒烘焙。茶叶的色泽成色,与炒功有很大的关系,不急不躁就行,茶叶便不老不黄。中国的茶叶品种多达近百种,但出名的也就那么几种,比如铁观音,信阳毛尖,西湖龙井,六安茶,碧螺春等。就色泽方面来说,不外乎有“红黄绿黑白青”六大茶类,两广一带喜好红茶,福建人喜好乌龙茶(青茶),江浙人喜绿茶,而北方人喜好花茶,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则喜好茶砖(黑茶)。一杯茶在手,多少话语的流转,都带着一缕清香甘甜,滋润了我的生活。看着茶叶的沉沉浮浮,我对人生充满了感悟:心随流水去,身与风云闲。
上一篇文章: 杭州医院好
下一篇文章: 儿童颈部肿块5实体病变非淋巴结肿大
《信阳文学》主编:杨扬执行主编:梁深义编辑:王羿付炜
投稿邮箱:QQ
信阳文学杂志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pressedflower.net/kcrhjc/5746.html
最新文章
今日推荐
- 没有推荐文章
热点关注
- 没有热点文章